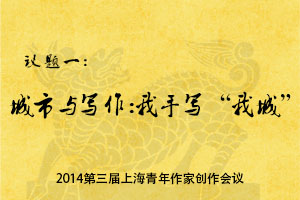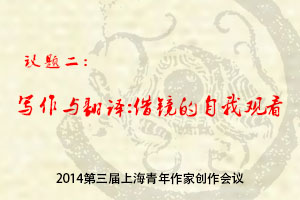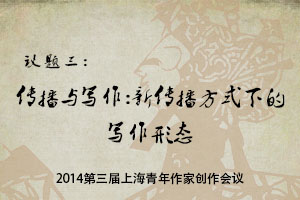青年作家哥舒意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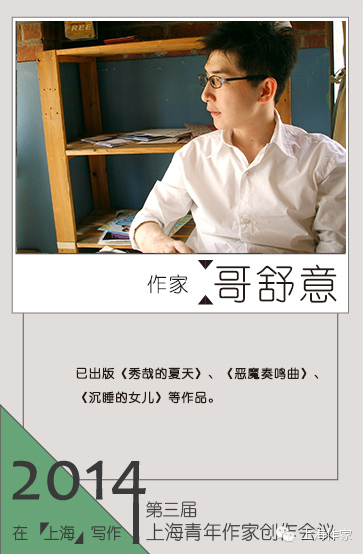
城市與寫作,我覺得更像是一種天然的選擇,因?yàn)槲疑碓诔鞘校谏虾I睿瑢懶≌f時(shí)候一定會(huì)帶著這種氣息,它是天然的東西,是沒有選擇的選擇。
我拿自己打個(gè)比方,我在上海出生,從一歲到九歲都在上海。從九歲到十八歲我到外地生活,一個(gè)二三線的小城市,一個(gè)被稱為華東民工之源的地方。但他仍然是城市。
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分開和割裂的,無論是在上海,還是在我父母的小城市,我呆在這兩個(gè)地方都會(huì)有時(shí)空錯(cuò)亂感。感覺哪里都不是我的故鄉(xiāng)。直到現(xiàn)在,我都覺得自己沒有故鄉(xiāng),我只是在這兩個(gè)地方生活過。

后來我認(rèn)識(shí)了一個(gè)新疆伊犁來的朋友,他有明確的家園意識(shí),他覺得伊犁就是他的童年、他的故鄉(xiāng),他以后會(huì)寫一本關(guān)于童年、青春和故鄉(xiāng)的長篇小說,也許是《天使望故鄉(xiāng)》那樣的,我很羨慕他。
從小時(shí)候開始,我就在尋找歸宿感。我喜歡上了讀書,大多數(shù)是外國小說,因?yàn)槲覐倪@些書里感受到了相同的氣息。中學(xué)時(shí)我就讀了一批法國小說,有趣的是巴爾扎克、雨果筆下的巴黎,一度讓我想起上海,他們所說的外省,就好像是我父母的小城市。也不只是法國小說,我在村上春樹的小說里,在菲利普?羅斯的小說里,在博爾赫斯的書里,在波拉尼奧的《2666》里,甚至是斯蒂芬金的犯罪小說里,都讀到了相同的氣息。
在我看來,哈利波特是具有城市氣息的魔法故事,王爾德童話是有城市感的悲劇美學(xué),王朔是進(jìn)化版的二三線城市故事,因?yàn)楸本?shí)際上就是氣派大一圈的北方城市。而我喜歡的國內(nèi)作家,寫的是標(biāo)準(zhǔn)的小城青春。
下一代的作家也許只能在城市里寫小說。隨著城市化的進(jìn)程,越來越多的人從自己的故鄉(xiāng)移居到了新城市。就像我身邊的朋友,他們的孩子離開了家鄉(xiāng),從小在上海生活,遠(yuǎn)方的故鄉(xiāng)對(duì)他們來說是個(gè)抽象的名詞,和遠(yuǎn)方的姑娘一樣抽象。他們提到一座城市,不會(huì)說這座城市是故鄉(xiāng),而只會(huì)說,我出生在那里,我在那里生活過一段時(shí)間。我喜歡那里,就跟喜歡其他城市一樣。
我自己是在寫作里找到歸宿的,小說就是我的精神家園。如果我從小沒有感受到它,如果它不存在,那我就創(chuàng)造一個(gè)。所以小說是我的歸宿,是我的故鄉(xiāng)和我的家園。不管我寫什么,寫青春成長小說、寫類型小說、寫童話等,將來人們?cè)谔岬轿业臅r(shí)候,應(yīng)該會(huì)提到我在上海生活。
我想,在以后的小說寫作里,故鄉(xiāng)作為精神家園越來越成為一個(gè)難以理解的命題。就像一個(gè)孤獨(dú)的游客,走出地鐵,站在水泥叢林的十字街頭,他回頭能夠看見的,只是一段又一段的漂泊。他不在這里,但也沒有了回去的路。所以,他只能生活在回憶里,關(guān)于一座城市的回憶,關(guān)于自己生活的回憶。
二三線的小城鎮(zhèn)已經(jīng)不存在了,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已經(jīng)不存在了,童年和青春都不存在了,它們變成了什么?變成了需要回憶而存在的東西,變成了我們這些人寫的小說。
謝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