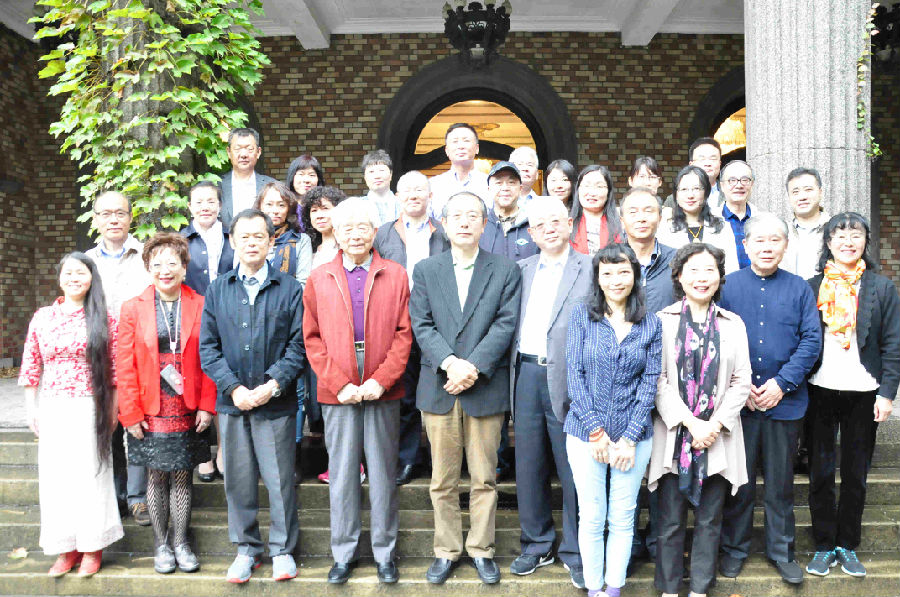您當(dāng)前的位置:主頁 > 作協(xié)動態(tài)
2017年10月18日13:50 來源:澎湃新聞 作者:楊寶寶 點擊: 次
海外華文文學(xué)在中國文學(xué)中一直占據(jù)特殊地位。華文作家身在異國他鄉(xiāng)外語環(huán)境里,卻堅持用中文寫作,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。
“世界華文文學(xué)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題材。”復(fù)旦大學(xué)教授陳思和認(rèn)為,如果要編一本2000年以后的文學(xué)史,“一定會排到虹影、陳河等海外作家。”
“在21世紀(jì),這批海外作家的作品在豐富性這個概念上影響到了中國文壇。他們在海外奮斗拼搏,等到他們回到文學(xué)上重新給中國文學(xué)提供作品的時候,他們提供的經(jīng)驗是嶄新的,我認(rèn)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豐富性。”
10月15日,第二屆“海外華文文學(xué)上海論壇”在上海召開,主題為“豐富的作家,豐富的文學(xué)”。來自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德國、捷克、日本、馬來西亞的10位海外華人作家與評論家共聚一堂,探討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(xué)對中國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的特殊貢獻(xiàn)。

論壇現(xiàn)場

上海作協(xié)黨組書記王偉
海外提供了作品發(fā)表平臺
大多數(shù)華文作家都將海外生活經(jīng)歷作為寫作的重要資源,在他們中間,虹影是非常特別的一位。
僅僅通過作品,很難把虹影看作是一位海外華人小說家。盡管她1991年就移居英國,代表作也都在這之后發(fā)表,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卻少有海外生活的經(jīng)歷,而是幾乎把全部目光投注在重慶和上海兩座城市上。重慶是她出生長大的地方,上海是她在復(fù)旦大學(xué)讀書的地方。
“回到這兩個地方,我從沒覺得自己有寫作障礙。”對虹影來說,出國不是積累寫作資源的過程,而是讓她“學(xué)會說話”。
虹影在自傳性小說《饑餓的女兒》中,坦承自己的非婚生子身份,曾經(jīng)她因此飽受困擾,備受欺凌,“從來都沒有說話的權(quán)利”,慢慢地,她對說話本身,也變得十分謹(jǐn)慎。

小說家虹影
出國之前,虹影已經(jīng)開始寫作,在地方刊物上發(fā)表過一些作品。因為自己“沒有名氣”,國內(nèi)當(dāng)時著名文學(xué)刊物還沒有發(fā)表過她的作品。
到英國后,她不想放棄寫作,就試著參加中國臺灣的文學(xué)獎,得了幾次獎,還去臺灣參加了文學(xué)會議,借此認(rèn)識了爾雅出版社的出版人隱地。她向隱地推薦自己剛寫完的長篇小說《女子有行》,收到退稿信。隱地說這本小說“太前衛(wèi)”、“看不懂”,但又加了一句話,“除非你能說服我。”
出書的渴望壓倒了不敢說話的恐懼,虹影寫了長信去解釋這篇小說寫了什么,《女子有行》最終出版,同年,又出了《饑餓的女兒》,虹影的小說開始受到關(guān)注。此后,她又努力在英國打開市場,寫英國人到中國的《K》和此前的《饑餓的女兒》都在英國取得不俗銷量。
“所以我想說的是,中國作家可以寫英國的書,而且中國作家不會怕這個時代。”

對海外經(jīng)歷,華文作家描寫角度各異
和虹影不同,更多海外華文作家還是把目光投注到自己生活的環(huán)境之中。異國他鄉(xiāng)的背景,是華文作家和國內(nèi)作家、讀者最大的身份差異,也是不少人依賴的創(chuàng)作資源。

作家穆紫荊
德國華文作家穆紫荊還記得自己1990年代過年回上海,百貨公司的營業(yè)員聽說她從德國回來,就興奮地說知道德國的幼兒園是什么樣的,一一給她講來。
“我一聽就是我寫的東西。” 穆紫荊當(dāng)時給《新民晚報》寫德國見聞,沒想到在她看來是日常生活的故事,卻被國內(nèi)讀者記得清清楚楚。
在上世紀(jì)八九十年代,出國還是一件艱難的事情,華文作家描寫海外生活的文字,成了國內(nèi)了解海外的窗口。
穆紫荊最初寫德國是無心插柳,日本華人作家李長聲寫作,卻是有意站在“讓中國讀者了解日本”這樣一個立場上。他1988年赴日留學(xué),旅日已30年,1990年代在《讀書》雜志開設(shè)專欄“東瀛孤燈”介紹日本,引起關(guān)注。
在日本生活多年,作品也均是寫日本,但李長聲說自己“對日本始終沒有親近感”,寫日本也始終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,目的則是為了讓中國讀者了解日本。作家止庵也曾評價,“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(tài)度。”
從這個目的出發(fā),李長聲寫的都是觀察日本的隨筆。他認(rèn)為日本文學(xué)的傳統(tǒng)是隨筆,日本就是“隨筆的”,用隨筆寫日本“再合適不過”。雖用隨筆的筆法,但他卻有意學(xué)習(xí)中國寫日本的傳統(tǒng),對中國人怎么寫日本,他很有研究,從《三國志》首次記錄日本,到近代學(xué)者黃遵憲、周作人對日本的著述,他均有拜讀。自己寫作,也力圖在前人的基礎(chǔ)上有獨特視角。

作家李長聲
“現(xiàn)在一些中國人旅日,時間或長或短,所見所聞互相重復(fù),觀察與認(rèn)識也未必超越前人。” 如今去日本已經(jīng)不是一件難事,但李長聲對大部分新的所謂“日本觀察”頗有看法。
有些華文作家的經(jīng)歷并不現(xiàn)世靜好,坎坷的經(jīng)歷成為作家難得的“財富”。加拿大華人作家陳河1994年有一段在阿爾巴尼亞做藥品生意的經(jīng)歷,在那期間阿爾巴尼亞發(fā)生了一場嚴(yán)重動亂,街上人人持槍,中國緊急撤僑。這段經(jīng)歷雖然短暫卻成了他小說中最為重要的題材。
《香港文學(xué)》總編輯陶然出生在印尼的萬隆, 17歲回到中國,在北京接受了兩年中學(xué)教育,進(jìn)入北京師范大學(xué)中文系,這期間經(jīng)歷了“文革”。后來他來到了香港,不會說廣東話,謀生艱難,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寫小說,走上了寫作道路。
“讀了他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寫大陸也寫香港,也在散文中回憶他印尼童年的少年的過去。三段人生對他的創(chuàng)作產(chǎn)生了復(fù)雜的混合影響。”南京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教授劉俊認(rèn)為,地球村的趨勢日漸明顯,作家到處遷徙、移民、旅行,文學(xué)的邊界包括呈現(xiàn)的形態(tài)都會有復(fù)雜性,陶然是這一趨勢下典型的早期代表作家。
全球化形勢下,華文文學(xué)該走向何方?
離開故鄉(xiāng),對于身份認(rèn)知的重新定位、異國文化產(chǎn)生的沖擊都是華文作家開始創(chuàng)作的“原動力”,但在這樣氛圍中發(fā)展起來的華文文學(xué),卻顯示出了“后天不足”的一面。
“新移民寫作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,已經(jīng)走過了書寫懷鄉(xiāng),漂泊,文化沖擊階段,新時期的文學(xué)應(yīng)該寫什么?”這是美國華人作家黃宗之提出的疑問,“如果今后我們都把寫作的題材轉(zhuǎn)向國內(nèi),那么新移民文學(xué)很有可能會失去他存在的價值。”
“海外作家應(yīng)該保持海外特性。” 劉俊教授也強(qiáng)調(diào)這一點。隨著海外作家開始參與國內(nèi)文學(xué)獎,在國內(nèi)文學(xué)刊物上發(fā)表作品,劉俊認(rèn)為華文作家在慢慢被“同化”,隨之帶來的問題就是,讀者對國外了解越來越多,華文作家如果不能保持海外特性,寫作題材的新鮮度就會慢慢喪失,“長此以往,變成大陸文學(xué)在海外的一個分支,那樣華文文學(xué)的價值的意義其實可能會受到折損。”
復(fù)旦大學(xué)教授陳思和則認(rèn)為,“‘豐富的作家、豐富的文學(xué)’不是說作家口袋里的豐富,說的就是在文學(xué)的精神上,在為中國人提供的精神糧食上,華文作家提供了豐富性。”

陳思和
不少海外作家在上世紀(jì)八九十年代出國,他們的思維結(jié)構(gòu)和如今國內(nèi)成長起來的作家有明顯差異,陳思和認(rèn)為這也是海外華人作家的優(yōu)勢所在,“我們今天在世界華文學(xué)領(lǐng)域當(dāng)中有影響的作家,很多都是1980年代后出國的。這批海外作家的思想追求、人格錘煉,大多數(shù)都是在1980年代形成的。陳思和認(rèn)為,海外華人作家在相對貧乏的生活環(huán)境之中,依然有強(qiáng)大的精神力支持,這是華文文學(xué)的獨特之處,“當(dāng)我讀到他們的作品,深受震動,他們還在寫這樣的內(nèi)容。”